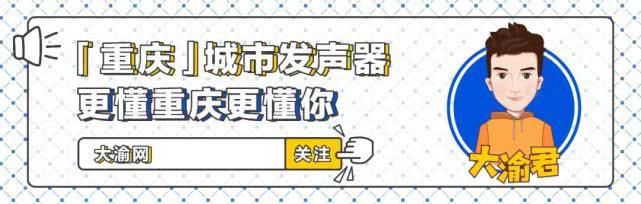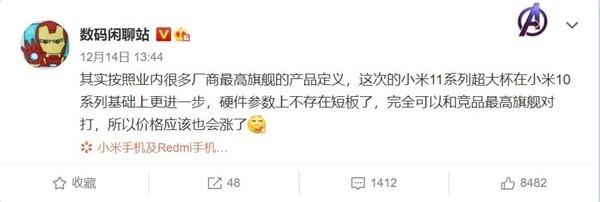当代中国舞蹈概念丛的真值空缺( 八 )
语义序列均不明的“中国民族民间舞”中 。
既然错误显而易见 , 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种从句法到语义的错误指称泛滥成“约定俗称”?是把握话语权的讲话者 , “同讲话者意谓事物的方式有某种关系” , 即所谓“句子意义派生于言者意义” 。 “词语不像树上的苹果 , 耐心地等待我们采摘” , 在世界各国的舞蹈词典中 , 没有“民族民间舞”之一名词 , 它“不能先于讲话者而存在” , 它“是某种决定的产物” , “不大可能是人的躯体(肾、脚趾)赋于词以意义的” 。 也就是说 , “中国民族民间舞”的称谓不是自然生成的 , 而是由当代中国舞坛上把握话语权的“讲话者”“决定”的 。 这种决定或者为讲话者迫于社会语境的压力(吴晓邦先生对创造这一名词时的自述) , 或者为后来人只用“躯体”而非通过“心智”使之变为约定俗成 。 我们强调舞蹈是用头、躯干、手、脚四信号构成的“关涉世界”的身体语言——而非去掉“头”的“肢体语言” , 就在于强调舞蹈——特别是作为已经形成身体母语的传统舞蹈不是自然生长的苹果 , 而是人类智慧的身体结晶 。 身体如此 , 关于以身体为媒介的舞蹈概念的确定更应该如此 。
无论如何 , “中国民族民间舞”这一错误的名称已经从社会层面到个人层面被广泛使用(比如北京舞蹈学院“中国民族民间舞”的学科命名以及教授和研究生们关于“中国民族民间舞”的探讨) , 话语权取代了语言权 , 在语用学上似乎形成不可逆转之势 。 于是 , “我们现在懂得什么是言者意义了 。 这是意在使人们基于辨识你的意向而形成信念”:既然我们不承认少数民族具有古典舞——而它们又在事实上存在(如有别于一把筷子的一筷一碟的蒙古贵族的“筷子舞”、有别于“果谐”的藏族贵族的“嘎尔”与“囊玛”、有别于“刀郎木卡姆”的维吾尔贵族的“十二木卡姆”) , 所以 , 就把它们与其民间舞一起打包、并且和汉族民间舞再打包 。 这样 , “你就需要发明语言填补证据空缺 。 因此 , 语言的存在是因为证据消失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获得 。 你的信念可以超越时空而存在 , 尽管这些信念所基于的证据局限于特定的时间与地点 。 所以 , 你可以利用存在的信念说服他人像你那样相信” 。 于是 , “中国民族民间舞”就成为了被某种“信念”所诱导的强制说服的“约定俗成” , 使“意义依赖于拥有者” 。
推荐阅读
- 明星|男明星的发型有多重要,多位代言人中国风小视频,邓伦真是一言难尽
- 姐姐|恭喜!中国又一游泳名将公开恋情,女友身材高挑长相貌美气质极佳
- 基努·里维斯|冒天下之大不韪!又一位艺人人设崩塌,中国的钱他是别想挣了
- 张常宁|中国女排第一美女即将大婚!提前穿“婚纱”,婆婆神似董明珠,家缠万贯
- 谷爱凌|“天才少女”谷爱凌: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,坐拥千万独栋别墅
- 陈情令|2021泰网评选TOP1中国男星!周生如故火爆全泰,陈情令CP烧不完
- 老明星|“毕竟我还要嫁人呢”!舞蹈一姐坦言“从不陪大哥”!并指出正直博是渣男!
- 赵丽颖|赵丽颖穿中国风旗袍,尽显中国传统经典之美!秒变性感小女人
- 国籍|女模钱凯丽:拒绝承认中国血统,却想在中国捞金,遭全体网民抵制
- 钟汉良|她是中国第一美人,连续8年荣登全球百美榜,如今36岁低调结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