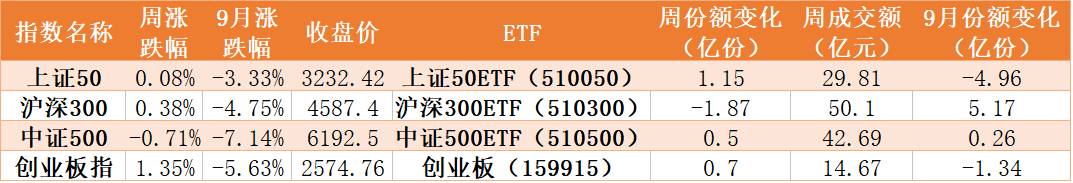“科学发展对世界观不会有根本影响”
南都:我在您一个访谈里看到,您现在还会蛮时髦地去上网课,比如科学类的,去听《量子力学导论》,为什么有这方面的兴趣?
陈嘉映:就是有点好奇心。读书可不就是好奇心吗?在哲学圈里,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还是挺多的。这么说吧,哲学涵盖很广,在这一端比较接近艺术、诗歌等等,另外一端接近科学。我个人学无专攻,对好多领域有兴趣。
南都:最前沿的科学,比如生命科学、宇宙科学、物理学,最终会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吗?
陈嘉映: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挺多的,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。在一端,有的人认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念,我偏向于另外一端,不觉得科学的常规发展对我们的世界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。科学有革命性进展的时期,17世纪、20世纪初的物理学,20世纪中叶以后的生物学,这些时期科学发展对我们的一般世界观念的影响当然比较大。Al的发展,脑机接口,这些也会有影响,不过是以相当复杂的方式产生影响。
南都:早两年有一个新闻提到,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修改,使得艾滋病患者的下一代获得病毒阻断能力。人为操作人类基因,会带来一些伦理学上的问题吗?
陈嘉映:当然,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大的伦理问题,到处都在讨论这些问题。尤其像基因剪辑这类技术,跟一般的科技发展不太一样,因为它动到人自己身上了,还不是只动身体,动到了整个的人,整个人格。技术乐观主义者更多看到技术造福人类,甚至会把动到人本身的技术看做对人类的“改善”。我和很多人则担忧更多,很多担忧就在眼前,比如工程技术引发的生态改变,无人机技术可以广泛用于暗杀,基因技术可以造出一种新的“人”。还有一般的社会问题,我读到2017年12月《自然杂志》上有一篇17位考古学家发表的文章,说是一万年来,技术创新总是拉大财富差距。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担忧:技术的迅疾发展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变化。这可能是更大的威胁,人家问你,你说有什么危险,你说不出,可等大家说得清楚了,已经太晚了。有的危险能说清楚,有的说不清楚,但是都值得高度重视。
南都:那么在现在这个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,哲学家或者“哲学工作者”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担负着怎么样的责任?
陈嘉映:我不觉“哲学工作者”有什么特别的责任。我倒不是说,哲学被科学挤压,已经变得insignificant,所以哲学不用担太大的责 任,科学到处受到重视,应该让科学家去担负责任。我更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。在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中,观念来自上层,圣人们、哲人们,他们work out一些观念,一层一层向下传播到整个社会,影响社会。所以他们有教育社会、引领社会的责任。也许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这样想,比如新儒家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哲学家应该有这种使命感。但在我个人看来,社会观念的形成和传播方式早就变了,不是在高层形成观念,一层层往下传播,没有这种社会机制了。你一个大学教师,能有多大影响?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,他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,还从为天地立心来想象一个思想者的责任,我觉得挺古怪的,不太切合实际。
你要说有什么责任,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。我指的是,你是一个老师,尽可能把你的课讲得好一点,你写作,尽量写得诚实一点,通顺一点,能深刻一点当然更好。如果你做翻译,尽量把它都翻译正确。我算稍微有一点社会影响,那么对公众讲话,对年轻人讲话,会想着,能够帮助到谁当然最好。有听众,有读者,告诉我他受益,我听到后感到安慰,也就是帮到这个人那个人,谈不到对未来人类社会负有什么特别的责任。就是你一个普通人的责任。
“疫情暴露出社会心理结构的脆弱”
南都:面对新冠疫情,作为哲学家您有哪些思考?
陈嘉映:我不作为哲学家思考。我当然会有些我个人的想法,也没觉得我想得格外多或者格外有意思。想到一两点别人不大说的。比较起历史上的几次流行病,新冠疫情杀伤力不算很大,比如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比,或者跟艾滋病比,当然艾滋病不是流行病,是个长时段的传染病,但加在一起杀死了很多人。但是,在新冠疫情之前,很多人不知道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,虽然它致死的人数多得多。不过就过去了一个世纪而已。
推荐阅读
- 如何直观地说明汉朝到底有多强大?
- 罗素:对平庸的崇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之一
- 深度阅读,慧眼识金,找到宝藏
- 把“穷”与“富”拆开看,原来如何致富古人早告诉我们了,千年无人知
- 经工集团党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
- 很快,我们的古典乐、民乐都将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延续。“
- 成语故事:牛角挂书
- 诗鲸2068《每一个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》
- 油画中的美人都跑了出来,就藏在我们周围,你能发现她们吗
- 一代儒将诗意雄安






![[突击晓分队]16年来头一回见,美军嗅到危险味道?大批轰炸机紧急撤回本土](https://imgcdn.toutiaoyule.com/20200426/20200426013242345786a_t.jpeg)